身不由己意思解释及造句(男人说身不由己的意思)
- 经典美文
- 2022-03-12 09:06:10
- 6684
9
羽市机场正下暴雨,飞机无法按照预定时间降落,备降机场流量已满,所以我们将飞返商市。提示音还未结束,机舱内已一片喧哗。我坐在机翼安全门靠近舷窗的位置,座位的空间很宽敞,足够伸展双腿,但我没这么做。这个密闭独立的空间里,我总以为自己在往前高速移动,飞机从一片蔚蓝飞往另一片蔚蓝,如果不是机翼略微的倾斜,还有那种微妙的失重感,我可能还意识不到这半个小时以来,飞机一直做着笨拙的盘旋动作。从窗外望去,云彩形状莫测,天际边隆起的部分如即将腾空的猛兽,巨大的作用力将它脚下的支撑面踏出无尽的波澜,即便如此,它们依旧看起来十分静谧,因此,我无法想象这些叠嶂的云层下方正大雨倾盆。我更想知道飞机上广播播放的声音究竟是提前录制好的,遇到哪种情况,选择哪段录音播放,还是由机上某位空乘现场播报。
座椅靠垫不断被人轻轻拍打着,身体不由自主地随之颤动,我没有转头,那个五岁左右的小男孩从登机后就没安分过,先是大声叫喊,接着又在走道上来回跑动,伸开粗短的双臂做着滑翔的动作,不管飞机处于地面还是空中,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游乐场,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做任何事。他妈妈对他说话的语气极其温柔,甚至让人觉得乏力,每一句制止的言语都显得形式主义。在我身旁坐着的是一个年轻人,头发精心梳理过,可能还上了些发胶,被灯光照射的部位都微微发亮,他穿着整齐,是一名服装设计师,坐下后跟我搭话的第一句就表明了身份,他说自己正要去羽市参加一场设计大赛,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这种规模的比赛,希望一切顺利。据说那边正在下暴雨啊,他刚上飞机就担心航班飞不了。我庆幸当时没有顺着他的话接下去说肯定没问题,都登机了,待会就会起飞,总不可能中途返回吧。是啊,从手机的天气预报里可以查到,我如此回应他。只是,当时我侥幸地以为夏季的暴雨很快就停,连绵不断的是春季梅雨。预计的航行时间是八十分钟,现在增加了一百一十分钟,在空中飞了三个多小时后,我们将回到起点。
我从来没遇过这种情况,那个年轻的设计师在我身旁发出声音,他没有把脸朝向我,而是伸长了脖子望着机舱的前端。不少人已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那里除了飞机的蓝色显示屏显示着外界温度零下二十度以及海拔高度八千八百五十米外,没有提供其它信息。现在遇到了,我说。在内心深处我比他还无奈,这次的航行对我来说是一种逃跑,逃离原有的生活,逃跑意味着对现状没有能力改变,这种逃跑又充满了不确定性,对未来也没有太多的期望。在飞机上又没法给组委会打电话,这下肯定要迟到了,他说着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发亮的屏幕,手指不断在上面滑动,恨不得把飞行模式切换掉。这也没办法,只能等飞机降落了再联系了,我说着毫无安慰作用的话。嗯,除此之外我也别无选择。你说刚才播音的空乘有没有在这趟航班上,我问他。哪一段播音,他问,从起飞到现在好几段呢。刚刚那段,提示飞机返航,我说。她当然还在飞机上,总不能播音完毕就打开舱门跳伞了吧,这样说起来,不管播报哪段播音的空乘都还在飞机上,他露出了笑容。难道播音的不都是同一个人吗,他接着问。好像声音不怎么一样,也可能是我听错了吧,我顿时充满了自我怀疑,我没注意到之前的那些声音。可能是我提问的方式不对,而且这种问题本身就不聪明。我还在回想那个声音,女性中音,却富有磁性,每个音节都在她的喉咙里滚落,如海边的沙粒般细腻,带有质感。我不应该想到海,我对它没有任何好感,即使它和她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
机组人员从机尾推出餐车,依次向乘客们分发小包装的零食,里面寥寥几颗极可能是限量版的坚果,像是某种奖励,奖励乘客们不吵不闹。孩子们得到了带有卡通长颈鹿图案的简易版拼图后,也都纷纷安静下来。我观察每个目所能及的空乘,她们身着统一制服,身材按照一定标准挑选,似乎妆容也统一培训过,虽然我很难判断她们的真实样貌,但从眼神上可以确定,没有任何熟悉的成分,这稍稍让我安下心来。一阵阵塑料包装被拆开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过后,机舱内的灯光暗淡下来,我也想办法让自己进入睡眠,小幅度偏转脑袋和身体的位置,摆脱腰部的悬空感,后脑勺也努力地左右平移,企图找到更舒适的姿势。然而,尝试了几分钟后,我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那段声音经过话筒和扩音器的转化后,穿透力十足,它依旧在我耳边缭绕,它像极了李静的声音,当然,此时她不可能出现在这里,但她的形象凭借这个声音在我脑海里重现,让我无法摆脱。
提示飞机即将安全着落,抵达终点,不,回到起点的声音跟刚才完全不同,一个年轻清脆的女性声音,我几乎可以猜测出是刚才所观察的哪位空乘。如果起飞阶段有种摆脱地球引力,逃离地球的感觉,那么现在就处在明显失重的状态,我厌恶这种感觉,特别是最后着陆时与地面的接触,遇上技术差的驾驶员,这种接触就变得生硬甚至粗暴,有时飞机不止一次地撞击地面,虽然都只有一瞬间,却让我暂时无法呼吸。飞机在地面上滑行一段时间后,开始播放舒缓的曲调,总让我感觉音乐像在表达一种劫后余生的愉悦。机舱内通电话的声音已经此起彼伏,大多用失望的语气对手机另一端解释造成现状的原因,只有我身旁的设计师的声音听起来一点都不失落,他双手捧着手机,不断地点头,对着话筒道谢。看来有好消息。组委会同意明天让我单独参加比赛,他告诉我,眼睛里闪着光泽。真不错,我说。是啊,我现在还多出了点时间修改修改原来的设计稿,这应该不算作弊吧,他又笑了。他解开安全带,起身从行李架上翻找自己的行李,随即取下一台被厚实的外壳包裹着的平板电脑。原来以为没时间了,就不打算做大范围的修改,现在到明天还有这么长的时间,我可以重新设计,他说着用一只白色的触控笔在屏幕上画线和调取色块,那些体现服装造型的曲线是他最先画上的,而简单勾勒的人物骨骼纤细,小巧的脸部没有眼睛,眉骨和鼻子组成数字7,嘴唇的位置则仅仅只是两抹较粗的短线。我发现他平板电脑的相册里保存的那些设计图稿,人物无论是身高还是长相都很相似,虽然摆出的动作各异,仔细看也只是一堆符号和等分线的组合,在他的设计世界里,真正发生变化的只有服装的造型和颜色。设计师似乎可以为图稿中的一切事物赋予生命,而不是人。
飞机完全停稳后,我才注意到自己的手机里有几条提醒未接来电的短信,这些加了下划线的蓝色数字都是同一个号码。我对它们的记忆还停留在几个小时前赶往机场的出租车内。
成排的楼宇在整齐的灌木丛后面褪去,我望着窗外,故作镇定。驾驶座上出租车司机的长相我没有看清,通常来说,他们都喜欢跟乘客聊天,多半是些低俗的笑话和未经证实的政治消息,而且两者内容差别也不大。我希望自己在这辆出租车里,也只是今天众多乘客中的一个,中等身高,中等体型,中年。刚上车的时候,出租车司机对我说过两句话,一句是请问您要去哪,另一句则只有一个哦字。一路上遇到三个红灯,他都再也没有说话,也没开车载广播,所以车里没人讲相声。我能听见他换档时,档位底座发出生涩的吱呀声,挡风玻璃前的那小尊弥勒佛咧着笑嘴,车内算得上十分静默。这时手机铃声就显得特别响亮,我看了一眼,一个完全陌生的号码,我猜测要么是地产开发商的新楼盘推销,要么是五花八门的理财销售,我没有必要接起。很快,出租车抵达机场二楼的出发层,我支付了多于显示屏上的数字的费用,并向出租车司机摆了摆手,说不用找钱,才看清他满脸通红对我说了第三句话,谢谢。这也是我和他之间最后的对白。如果不是血压过高,只能是他正憋着尿的缘故,我暗自思忖。
机场内部的设计从来不会考虑光学污染,在这个开放的环境里,光滑的地面,光滑的天花板,光滑的自动玻璃门,光滑的屏幕,光滑的桌面,光滑的墙体,光滑的灯泡,没有一个平面不在反射着光线,多余的光线。在散乱的光线和急于离开的人群之间穿行,从来都没有可以躲避的空间,我不得不紧盯地面,那些细小肮脏的缝隙,生锈的行李车滚轮,无数只成对移动的鞋子,随着我脚步的加快,单肩包紧贴着肩膀的那片减压垫就会向后滑动,直至我感觉到行李的重量无端增加。
请给我一张机票,我说。虽然行李只有这么一个单肩包,但背着它一路小跑,找到售票点也花了我不少时间和体力。请问目的地是哪里,坐在柜台后面的售票员抬头看了我一眼问。我赶紧把脸别开,俯身说,去哪都可以,只要给我一张机票。先生,这样我没法出票,请告诉我您要前往的目的地,我可以帮您查一下航班时间。不管去哪,我要今天最早起飞的那趟。那趟零点的时候已经飞走了。我不觉得这是幽默,她明明知道我的意思,不过我只能重新表达一番,我要一趟现在开始最早起飞的航班机票。那样您赶不上登机时间,登机口半小时前就关闭了。我要一张能让我最快离开这里的机票,我已经涌上了几分怒气。这我没法保证,您知道的,如果遇上航空管制或者什么特殊情况,谁也不能保证哪架飞机先飞,您只能按航班时间购买,她的语气里有些不耐烦。我只想要一张尽快起飞的机票,去哪都成。这样我没办法出票,请您谅解。我和售票员之间的对话陷入了一个怪圈里,她愿意卖一张机票给我,她当然愿意,她的工作就是这个,前提是我需要告知飞往的城市。我想买一张机票,却不知道自己想去哪。后面排队购票的旅客已经略有微词,我不得不立即从脑海里搜索出一个适宜的地点。目的地是羽市,航班时间是今天早上十一点,我得尽快更换登机牌。售票员最后给了我一个服务性笑容说,刚好有人退票,您捡了个漏,运气真好。
无论飞机本身的颜色多么单调,尾翼都不会是纯白色,它们色彩艳丽,在陆地上不管是静止还是滑行,它们的作用都是向旅客们展示商标。我的登机口在三号,旁边则是三十号,之间的过道没有任何座位,一眼就能望见尽头,透过候机室的玻璃窗,看到这些帆船般的飞机尾翼,我才松了一口气。因为临时买的机票,距离登机时间已经有点紧迫,我过安检走的是快速通道,还插了队,而登机口又在机场的最里侧,我一路奔跑,在光亮的大理石地面上跑,在电梯上跑,跑得比那些付费的四轮电瓶车还快,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往前奔跑并不为了赶上一架即将起飞的飞机,而是身后有头正在追赶我的猛兽,它像我身体在地面上的倒影那样,紧跟不舍,甚至即将从四面八方向我扑来。一停下来,四周的一切似乎都在膨胀,我不知道视觉的焦点在哪,其他乘客在不远处,无论站着还是坐着,我都觉得他们跟我之间有种排斥的力量,他们是弧光的一部分。
我看见有个修长的身影拖着巨大的行李箱从另一端朝我走来,背对着光线,我一时看不清样貌,只能看到身体剪影般的轮廓。这么巧,她摘下墨镜露出一对精致的杏眼,对我说道,发现一路跑来的是你,吓了我一跳。在候机室遇到娜娜确实让我感到意外,她一副中性装扮,黑色套装把她白皙的皮肤衬托得更加光亮,而且它还很贴身,显得她很干练的样子,而她的一侧脸颊的轮廓还被光晕笼罩着,看不清边缘。在我的印象里,每一次与她见面,她都能带给我一些好运气。我赶飞机,我还喘着大气。换登机牌的时候,你就应该先托运行李,她说。为什么,我问。翻墙之前先把帽子扔过去,每一次,我觉得自己快赶不上时,都会先办理行李托运,只要行李上了飞机,他们就会等你。我没试过,但他们为什么要等呢,时间到了就关闭舱门,在我的印象里,飞机从不等人。那要看对他们而言,你的重要程度了,她笑着答。我当然一点都不重要,你也去羽市吗,我问。不,我出国,有演出。什么演出,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关心,但还是问了这个问题。戏剧,我在里面得饰演两个角色,而且她们的性格完全不同。双胞胎吗,我问。不是,连长相都不一样,这对我而言实在是个挑战。听起来确实很有难度,我对表演一窍不通。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跟娜娜聊天能让我暂时忘记自己的处境,甚至忘记我急着离开这里,四周的光线也变得不再让人讨厌。
如果演员和观众之间有一堵墙,我们把它称作第四堵墙,有人说演员需要建立起这堵墙,进入当众孤独的状态,又有人说应该推倒这堵墙,让演员在戏里和戏外自由出入,而我思考的是第五堵墙,它在我的这两个角色之间,我思考的是该推倒它,还是该建立它,娜娜抬起双手,两只白皙温柔的手掌划出二十厘米的空间,不断在我面前从上往下移动,她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我几乎听不懂的内容,眼神并没有看我,更像是自言自语。我知道这种状态,通过描述问题,以达到在描述的过程中解决的目的。我就经常扮演另一个角色,我说。我老早就看出来了,她表情严肃地说,也许你扮演过好几个角色呢,一个角色用在公司,一个角色用在家里,一个角色用在我面前。照你这种分类法,可能就不止这么几个角色了,我能凭借这种切换自如的表演拿点什么电影奖项吗,比如最佳男主角之类的,我问。当然不行,你的表演总让人感觉用力过猛,真正的大师级的表演是不着痕迹的,她大笑起来,嘴角露出一串迷人的细小的凹陷。你说三十号登机口为什么在三号登机口旁边,而且国内登机口和国际登机口紧挨着,好奇怪,它们之间才应该建一堵墙才对,我随口问道,我不知道自己潜意识里是不是想扯开话题。那要先弄清楚祈祷室为什么挨着女卫生间,她说着指了指我身后的那段电梯旁的小房子,从门上方那一个跪着的小白人和两个站着的男女标志上,可以判断依次并排的是祈祷室,女卫生间,男卫生间。我可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不是基督徒。如果祈祷室挨着男卫生间,那肯定也有人问这是为什么呢,跟你的登机口问题类似。这是你的诡辩术。话说回来,你上次的表演怎么样,她问。什么表演,话已经说出口,但我马上明白她指的是什么,哦,还不错,对我来说算是有惊无险,对了,谢谢你的帮忙。那没什么,你好像该登机了,她指着我身后说。三十号登机口已经排了条长龙,有个不安分的小男孩子不断从队伍的前端奔跑到后端,接着又返回,如此往复,让我想起某道跟苍蝇和自行车有关的趣味数学题。光顾着跟你聊天,我都没注意听提示音,那我先走了,我与她道别。看样子,你要消失一段时间了。什么,我经常无法捕捉娜娜的那种跳跃性思维。飞机在空中的那段时间,乘客无法与地面的人取得联系,对地面的人来说,乘客从地球上消失了,她说。这只是暂时的,我可不想永久消失,我说,开始检票了。每次都有急事的样子,我听到她在身后小声嘀咕。
机舱内又响起了那个富有磁性的女性声音,她提醒乘客们,如果条件允许,飞机在补给完成后,将再次飞往羽市,所以请大家坐在机舱内等候。话音刚落,四周又是一阵喧哗,这次还夹着手机呼出时的嘟嘟声,有人开了扩音器。机舱内慢慢变得闷热起来,不时有人向机组人员抱怨着什么,比如为什么没开空调,为什么卫生间一直处在关闭状态。而我再一次想知道这段声音的来源,它究竟属于谁。我的颈部开始冒汗,还有最靠近脸颊的耳屏也有汗液滑过的感觉。突然,我的手机铃声响起,又是那串号码,屏幕上那些数字看起来像几只排列整齐的苍蝇,挥之不去。
哪位,我接通手机,故意把声音压低,几乎不带一丝温度。您好,请问您是郑颖吗,对方说,我是您的妻子李静的律师。是我,你,你是律师,我重复了一遍他的职业。对,早上本应该给您妻子打电话把这事再确认一番,可是她没有接听,他说。什么,我提高了音量,他这些话的意思并不难理解,但我听完,瞬间感到脑袋发懵。不过没关系,之前已经确认过了,她嘱咐过我今天给您电话,我想想还是直接打过来就好了,他接着说。你说了一大堆话,绕来绕去,究竟想说什么,我生气地问,也许我只是想用愤怒来掩盖我内心的慌张。您的妻子想跟您协议离婚,自称是我妻子律师的家伙这么说,电话那头,他的语调十分平和,甚至有些冷漠。这不可能,我朝话筒喊道,这不可能,你一定搞错了。如果不是机舱里本身就吵杂,我的声音应该会引起很多人注意,现在注意到它的只有身旁原本低头对着平板电脑,正在改设计稿的家伙,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我会寄一份协议到您的办公室,跟您确认一下邮寄地址,应该不会错吧,接着,律师很不熟练地报上了一长串地名和邮编。你一定搞错了,我继续大声嚷道。您是说刚才我说的协议邮寄地址错了吗,邮编呢,不然您再重新给我一遍。不,整件事都错了,地址是我的公司没错,但整件事肯定搞错了,我的妻子不可能想跟我离婚。很多当事人都会这么说,我也可以理解,但必须解释的是,我们手里有照片证据表明您在外面有其他的女人,他说。什么,就因为这个吗,我瞪大了眼睛,感到很是诧异。这个理由已经足够充分了,他说,当然,我想您妻子也是因为顾全您的名声,所以决定采用协议离婚的方式,您到时先看看协议里的条款吧,有什么事再联系我。没等我回答什么,律师已经挂断了电话。
我握着手机的手开始颤抖起来,食指正好处于侧面的锁屏键上,便习惯性地按下这个按钮,黑魆魆的手机屏幕里只有我阴沉的倒影,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孤独感。过了一小会,我感觉口渴,喉咙发紧,我想喝水,最好是冰镇的汽水,这种渴望让我摁亮了头顶的服务灯。一名空乘从机舱后段走来,她问,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汽水,给我一杯汽水,我说。好的。不,还是给我一杯温开水吧。好的,请您稍等。对话的过程,我都没有抬头看她,但这不妨碍她接受这些信息。又有一小会,我想吐,我用舌头不断从干涸的下颚汲取唾液,吞下,企图凭借这不到一毫升的液体阻止胃部的翻腾。你没事吧,我听见旁边设计师的声音,他停下手里的工作。没事,我转头看着他,刻意把嘴角下压,让面部表情舒展一些。就在此时,我看到了那个折返的空乘,她一只手端着杯水放在胸前,另一只手的位置处于腹部,她走路时上半身挺直,甚至有点僵硬,我从没见过李静这样的姿态,除了性别,她长得跟李静毫无相似之处。我想起刚才她的问话,这种近乎机械的遣词造句的方式也不是李静可能说出的。她把盛有水的塑料杯递给我,您的水。我不知道她此时为什么要露出一抹微笑,这个笑容,这种调动上唇的方式,眼睑下压的角度,像极了李静嘲讽时的笑容。我没有伸手接过她手里的水杯,我觉得自己的手臂根本抬不起来。先生,您哪里不舒服吗,她问。没有,我只是想休息一下,我累了,我回答。那您的水还要吗,她又问。不需要了,我再次回答。事实上,现在我什么问题都已经不想回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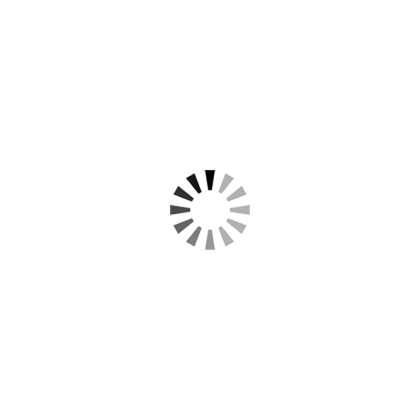
你的脸色不怎么好,空乘离开后,设计师的声音又一次传入我的耳膜,他已经把平板电脑收起,可能在等待飞机重新起飞,也可能在等待一些新的灵感。这不是一个问句,所以我没有说话。我一动不动地坐着,现在才发现自己一直没有解开过安全带,这条蓝色的带子紧紧地缠绕在我的腹部,银色的金属扣顶住我的髋部,在这个位置里,我比任何时候都稳固。这种错觉一直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后座的小孩又开始摇晃我的座椅,他站着,双手抓住座椅的两侧不断使劲,我没注意到他停止下来究竟是被人制止的,还是自己玩累了。我转头默默看着舷窗,机舱内的景象在灯光的作用下与机翼的一侧重叠,效果并不明显,毫不费劲就可以穿透它看见窗外的那片灰色的水泥地面,两排整齐的白色划线标识出跑道的方向,跑道中央有好几道飞机高速降落时轮胎留下的黑色胶印。再远一点是整片开阔的荒地,沙硕和野草则一直延伸到更远处的大海,白茫茫的一片,我在封闭的机舱里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正身处海岸边。
声明:久久散文网为非赢利网站,文字及图片版权均归作者所有,如相关信息侵权与违规请与本站联系,将在三个工作日内处理。
本文链接:https://www.99sanwen.com/n/43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