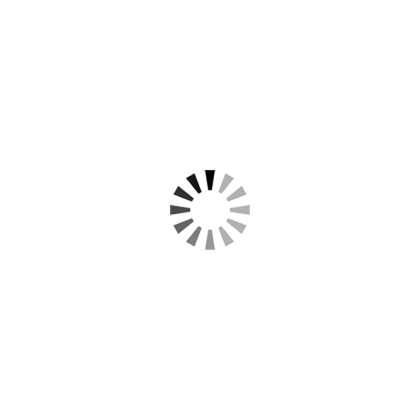晚春原文内容和诗意解释-晚春诗意思是什么
- 杂文
- 2022-03-23 19:40:11
- 4561
管琴(《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
2021年是王安石一千年华诞。一千年来,围绕王安石的争议似乎从未停止,他究竟是“一世之伟人”还是招致“靖康之祸”的祸首?他给后世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为了厘清上述问题,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千年王安石”专题,邀请多位宋史学者从政治、文学、哲学等层面多维度展示王荆公的面貌,以飨读者。

政治身份的王荆公最为有名,诗人身份其次。不过历史上对荆公诗人身份的肯定向来比前者为多。关于荆公诗,前人众说纭纭。其中或尚有可发明之处,于此聊陈一二。
一
荆公性情执拗,世所共知。才性与执拗体现在诗歌中,一是诗歌内容会导向唯有诗人本人能置足之地,二是处处可见文字经过安排的训练有素。
顾随为放翁辩护,讲放翁虽不是伟大诗人,却是真实诗人,因他能够忠于自己的感情。其实优秀的诗人大多如是,荆公亦然。拗之不掩饰,也是忠于感情之一种,荆公虽拗,并不戆,或者蛮。《燕侍郎山水》:“燕公侍书燕王府,王求一笔终不予。”为徐俯所欣赏,其中就有拗劲,并见文人气骨。
荆公诗多在支分条布上,显出与他人径庭之意。他常有一句之炼。一句是相对两句而言,非炼全部,而炼其半。倘若一句用寻常体格,另一句则用心安排,这样能在稳定中有所突破。七律因工于对仗,此种特点尤盛。《上西垣舍人》:“讨论润色今为美,学问文章老更醇。”后一句无论“学问文章”,还是“老更醇”,表达均属常见,而介甫以“今为美”对“老更醇”,“讨论润色”对“学问文章”,既贴切,与惯常用法又略有不同。荆公善于打乱语言组合的惯性,不过不至颠覆,整体还是以流畅的诗歌调性为基准,审美上不作偏激的游离。《次韵张唐公马上》颔联“病来气弱归宜早,偷取官多责恐深”,也是前句平常,后句振起。《次韵酬吴彦珍见寄二首》其二:“白日忆君聊远望,青林嗟我似逃虚。”前句语序如常,后句“逃虚”则用《庄子》意,陡起而意新。再如《次韵酬宋玘六首》其五,“遥思故国归来日,留滞新恩已去年”,以“留滞”对“遥思”,衬托不同境况,“留滞新恩”,亦自带况味。字面令人目光停留处,即是不同寻常处。另如《偶成二首》其二:“年光断送朱颜老,世事栽培白发生。”前一句的“年光断送”属常见句法,“载培”与“世事”连用,则趋新警。世事已颇费人意,白发渐生却使人心灰,字与字的排接之间,流露人生的况味。
王若虚称赞“两山排闼送青来”中的“排闼”,“读之不觉其诡异”。他另举山谷“青州从事斩关来”“残暑已促装”句,称此种就“令人骇愕”。荆公并不试图斩断诗歌意脉,也无意生造字词耸人耳目。一句之炼以外,还有正常的结构相承接。“排闼”之类,对仗甚工,却不知从何处拈来,显得像是透网之鳞。
据宋人诗话载,荆公论子美“无人觉来往”,“觉”字大好;“暝色赴春愁”,“赴”字大好。论字是诗人习气,荆公对字当更为敏感。“无人”“来往”“暝色”“春愁”几字,中间若不是“觉”“赴”连接,很容易就一笔带过了。王安石《即事六首》其六:“蜉蝣蔽朝夕,蟪蛄疑春秋。”试想这两句如果不是用了“蔽”与“疑”,那么关于时间的“蜉蝣”“朝夕”“蟪蛄”“春秋”等字眼,亦不会令读者的眼光多作停留。最无知无觉的蟪蛄也会陡起春秋之思,才是突破一般感时之作的奇异之笔。
提点江东刑狱任上,他写诗给孙觉。“区区随传换冬春,夜半悬崖托此身”。(《度麾岭寄莘老》)起句劈空切入,“夜半悬崖托此身”,写出夜行险境。“托”字,险中见出勇猛,又莽然。“陶令清身托酒徒”,(《狄梁公陶渊明俱为彭泽令至今有庙在焉刁景纯作诗见示继以一篇》)同样用“托”字,表示无拘检,见出不一样的陶潜。宋人尊陶、和陶甚多,大概还没有这样写过陶潜的。
王若虚“不觉其诡异”的赞叹,说明荆公诗的一种好处是,出常亦可妥贴,亦可自适。如果全以传统组织诗作,那么未免乏味,尤其律诗。句句无意外固不佳,句句新奇、发风动气亦令人目累。传统中有所更迭,方能进入理想之境。荆公擅长别创一路,如有一句相对平缓,则有一句有所振起。此等振起,并不是要偏离整体审美,全篇仍在同一诗歌基准线上跃动。这样,我们在阅读时,感觉它既属于我们熟悉的脉络,同时也有些部分“犹如人的双脚从未踏上过的陌生的地方”。(舍斯托夫《莎士比亚及其批评者勃兰兑斯》)
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称,王安石袭用李白诗句“白发三千丈”,变作“缲成白发三千丈”,何文焕指为大谬,“发岂可缲?”实则这里也是介甫刻意出新处。《木末》诗亦用“缲成”,“缲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李壁评:“如画两叠。”介甫不喜太白诗,太白说“天台四万八千丈”,他特意纠正说:“天台一万八千丈。”(《送僧游天台》)较真实在较得明显。马一浮讲“立心不容有纤毫夹杂,对人不能有些微迁就”,(《与张立民》)或可形容荆公做人与写诗的心态。诗人不但忠于自己的感情,忠于自己的想象,也忠于知识与常识的矫正。王安石有好争短长之名,琐屑处亦见其不能迁就之意。
中国诗的排列组合,往往写到上句,下句就会自然浮现,特别是对一位以集句擅长的诗人来说,可资的诗歌资源实在太多。高妙之诗人,往往自由择取他认为确切的内容,同时力避手熟。纳博科夫对写作者的创造力有过形象的评论:
作者对这摊杂乱无章的东西大喝一声:“开始!”霎时只见整个世界在开始发光、熔化,又重新组合,不仅仅是外表,就连每一粒原子都经过了重新组合。(《文学讲稿》)
诗人组织一首诗的语言时亦是如此。写一首诗,像是对一切散乱的语言材料进行了重新组合。诗的完成,是由杂乱进阶而成的魔法,也呈现出内在世界发光的结果。
二
荆公诗状物写景之清雅,还在于叙述角度的新异,这在宋人中独树一格。
许彦周早已观察到,“荆公爱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荆公善写水、写影,也善写流动。北宋词善写影,研究者已有注意。写什么不重要,全在于如何写。写影,本来容易写得轻浅。而荆公写杏花是“俯窥娇饶杏,未觉身胜影”,相比宋词常见写影,手段似更胜一筹。据陈师道说,介甫谓张先“云破月来花弄影”不如李冠“朦胧澹月云去来”,想是大概后者不那么写实,景物也不是呆呆地罗列。不单是水中之影,其他的水中视角也令他感到兴致盎然。像上诗写到俯窥娇杏的动作,全无软媚,自有风韵与容光。王安石欣赏苏轼的“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苏轼这两句写江面,像是浮于半空。万事无根如浮,似能撼动一切,这是荆公欣赏的诗境。他自己的“钟山石城已寂寞,只见江水云端来”,(《和王微之登高斋三首》其二)循太白《金陵》诗意,是出于同一机杼的反复创作。
雪天的景物尤能引发他的兴趣。“开门望钟山,松石皓相映”,(《己未耿天骘著作自乌江来予逆沈氏妹于白鹭洲遇雪作此诗寄天骘》)李壁注:“宋文帝登钟山,萧思话坐盘石弹琴,帝赐酒曰:‘相赏有松石间意。’”钟山诗写到松石常见,但专写大雪天场景,松石此等坚实之物竟如水中物之明洁,这是荆公专有的兴致。
视角也往往在水上,如被黄庭坚称赏的《法云》:
法云但见脊,细路埋桑麻。扶舆渡燄水,窈窕一川花。一川花好泉亦好,初晴涨绿深于草。汲泉养之花不老,花底幽人自衰槁。
汲泉养花,花底有为花倾倒的幽人,但幽人却比花更易于枯槁。荆公善写水与水中之植,写得掩映相生,有六朝与晚唐风格,却毫无靡态。
《步月二首》其二:
蹋月看流水,水明荡摇月。草木已华滋,山川复清发。褰裳伏槛处,绿净数毛发。谁能挽姮娥,俯濯凌波袜。
绿净可数毛发,形容婉妙。人在绿中,而为净绿所陶醉。有些是想象中的,有些则是实见;打并一处,迷离惝恍。
介甫诗中的植物与掬水之主体往往都是流动的。《新花》写“汲水置新花,取慰以流芳”,汲是动作,取慰乃是含情之抽象动作,流动之状态从水指向具体之人。《赠彭器资》“我挹其清久未竭,复得纵观于波澜”,其中包括有流动的水,以及为水的流动所吸引的人。《散发一扁舟》中的“秋水泻明河,迢迢藕花底”,历来为人所传颂。意象明洁,远绍十九首之意脉。钱锺书谓:“拜伦诗称美人:‘发色增深一丝,容光减褪一忽,风韵便半失。’与宋玉手眼相类,均欲示恰到好处,无纤芥微尘之憾。”荆公从水中着眼,专写天上地下流动之芳韵,以及无限之幽人幽怀,呈现的恰好之处与之相似。《移桃花示俞秀老》:“晴沟涨春绿周遭,俯视红影移渔舠。山前邂逅武陵客,水际仿佛秦人逃。”《秋夜泛舟》:“的砾荷上珠,俯映疏星摇。”目光是向下的,万象摇曳于水上,一切平静下来又还是一整体。《岁晚》中的“俯窥怜净绿,小立伫幽香”,也是写水上之花与香气,感受它们的是诗人本人,也是极安静的欣赏者。“俯观”“俯临”“俯视”等本为魏晋六朝诗常用。不仅是“俯”,荆公还善用“卧”。《北山》之“刳木为舟数丈余,卧看风月映芙蕖”,显出逸人之态。而且在诗人的笔下,天上也如水面一般,“天低绀滑风静止,月澹星渟尤可喜”。(《我所思寄黄吉甫》)将水、植物、星象、自然之香气等融在一处运思写意,背后则是别有幽怀的诗人。虚实之间,足见上乘。
糅合感官、物象、空间、时光,虚实起结形起的影像,为荆公诗擅长,尤其在他的五古、绝句中,往往用得如刃发硎。他的《弯碕》诗写到杜甫:“永怀少陵诗,菱叶净如拭。”在宋人对杜甫的赞美中,我们大概很少见到从这样的角度,忆及杜甫也是在水上。杜甫诗“菱叶荷花净如拭”的明净典雅,是“怀”的具体促发。《自喻》一诗,亦以水边之竹和水中之菱起兴:“岸凉竹娟娟,水净菱帖帖。”明净如菱叶,可视作诗人心境的自况。你不能不说他对少陵在那一刻,有真挚的理解与沟通。
三
荆公晚年诗为何能“脱去世故”,(陈岩肖语)似乎不难回答。长避钟山,遗远世荣,繁华略尽,已是诗人归宿。处山水之间,不再日与外物为角,清气渐渐涌上来了。荆公晚年心境,在当时大概颇令人揣测,《偶书》一诗云“每逢车马便惊猜”,《侯鲭录》举此句为证,猜测介甫“暮年犹望朝廷召用”,这大概是着于皮相的过度解读。
后世诗评家或指出介甫有学子美处,言其五言得子美句法。若论二人之比较,子美平生“嫉恶怀刚肠”,(《壮游》)荆公自然也有一段刚肠不能释去。子美造次不忘君,愈老诗愈峭拔;荆公则愈老愈清。若论荆公人生际遇之特殊,实为几百年间罕见,却不会如子美,道有“朱绂负平生”。(《独坐》)以彼之气傲,绝不至作此语。子美于世乱衰变有切身之感,自云“扁舟空老去,无补圣明朝”。(《野望》)荆公既脱去世故,誓不再返,诗中也少见形容往昔。论及往事,至多是“红葵紫苋复满眼,往事无迹难追寻”之类,(《光宅寺》)这里沉思的还并非自己的往事,不多予人怀想空间。
顾随说诗:“生的色彩浓厚、鲜明、生动,在古体诗当推陶公、曹公,近体诗则老杜。”老杜“生”的色彩,体现为对诸事安排与形容的浓烈。荆公性情虽拗,根株却厚。换种角度看,拗也是一种“生”之浓烈,只是偏于负面。荆公能识“生”的趣味,《䂬溪诗话》称荆公爱眉山“冰下寒鱼渐可叉”,此是一种生活趣味。《邀望之过我庐》谓:“知子有仁心,不忍钩我鱼。……岂鱼有此乐,而我与子无?”他并非像杜甫那样由热诚、仁厚而朴拙,而是显得更拗。这方面虽然有学杜的一面,但他有些古体写得实不如杜甫。比如《白鹤吟示觉海元公》:“白鹤声可怜,红鹤声可恶。白鹤静无匹,红鹤喧无数。白鹤招不来,红鹤挥不去。”质已足够质,却显得不够生拙。如果是杜甫来写,想必“生”的色彩会更浓烈,比如与之类似的、同样用乐府古体所写的《杜鹃》,就好很多。吉川幸次郎说王安石之诗“如其人品如其政治,有吹毛求疵的洁癖”,实在见解透彻。王安石之“洁癖”,于诗体现尤多,而其不足之处,也在于略显“吹毛求疵”。
荆公诗“生”之浓烈,或体现为气度清越,别有幽怀。《晚春》诗:“春残叶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盏疏。斜倚屏风搔首坐,满簪华发一床书。”风度清胜。洁僻不免生冷,而赠人之作的深挚却多少能淡化这种冷感。《谢微之见过》:“唯有微之来访旧,天寒几夕拥山炉。”情意雅切。与旧友相会,只是淡淡一句“天寒几夕拥山炉”,情感已自觉脱去一层浓烈。《梦黄吉甫》:“西城荠花时,落魄随两桨。岁晚洲渚净,水消烟渺莽。踌躇壁上字,期我无乃尪。”李壁概言此诗“皆情钟之语”。吴乔评论《送乔执中秀才归高邮》,感慨“介甫一生傲慢,如此诗一何温蔼也”。荆公性格刚烈自傲,怀人、赠人之作却倜傥而不失温蔼,同样是荆公本色。虽然自言“此身已是一枯株”,(《谢微之见过》)晚岁诗歌中却少露颓唐,亦无枯冷之感。反而清气粹满,刚肠亦化为绕指柔。
不可解者,清人刘宝书作《诗家位业图》,将介甫安于“苦行”诗人一列。同列其中者,唐有郊、岛,北宋则有梅尧臣、陈师道、叶梦得。不知刘宝书的印象从何而来。郊、岛寒俭,为苦吟鼻祖,以诗穷至死。列上介甫大概是因为拗折。但介甫于诗歌其实是最不喜“苦行”的。贾岛诗句“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看似也拗,但泛观荆公诗,实不会有知音不赏之叹。后人或谓其诗学“二谢”“三谢”,诸谢怎会是苦行呢?此为不可解。
四
王安石深不乐诗赋取士,人所共知。熙宁年间罢诗赋,取经义,固然有许多基于思想见解、以及现实政治考虑的解释,而王安石本人对诗赋有极高的感悟与掌握,却于特擅之事物不以为贵,足见其兀傲。只有才子能弃去一切,一切不屑为。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评论但丁:“作为诗人和个人,但丁的突出特点是傲气而非谦逊,原创而非守成,丰富或有活力而非节制。”其实这三种特点多为才子专属。王安石之擅集句,实在已到诗歌之极致,技巧方面既见顶,态度亦显出殊不为意。治平四年(1067)神宗即位,擢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司马光不愿接受。神宗说:“卿有文学,何辞为?”司马光曰:“臣不能为四六。”看似谦称,实乃自觉四六为壮夫不为。非不会,不为也。对于有大抱负的政事家而言,需要突出与重视之物是有限的,故能审于轻重特别重要。
王安石不喜诗,却能为之,至少王安石比司马光更喜吟诗,王安石之于诗比司马光之于四六则更为擅长。所谓“一个有艺术才华的人一生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当他找到一种表现特定主题的艺术形式,能在其中融合他自己的各种天赋”。(茨威格《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诗歌并非王安石唯一擅长的文体,当然他也不会觉得写诗是他的幸运,幸运的还是后世的读者。
严沧浪形容荆公集句《胡笳十八拍》,“如蔡文姬肺肝间流出”。前人之诗句典故,字词之排列组织了然,岂止是从肺肝间流出,简直是肺肝如揭。张戒批评他“只知巧语之为诗,而不知拙语亦诗也”。王安石固不会用拙,但巧也不算得十分巧,有时只是构思之巧,或者诗歌语言偏向某一向度而已。其实笔者觉得较为重要的一点是,他的巧并无自得之意。由此可以想到,荆公不会提炼诗法,北宋“夺胎”“换骨”这类技法提炼,绝不会为荆公所提出。他大概是最不会传授技法的一类诗人。
荆公才高,为诗人之一面,亦富有感情。此种感情并不显得浓烈,而以清气胜。古体比兴深远温厚,颇得风人遗旨,排比状物亦有雍容不迫之意。近体则精于一句之炼,善于嵌合传统与新知。山水诗得六朝与唐人之婉媚,浑然凝炼处亦得工部之神;咏古诗发扬而不失典雅。另像寄怀逢原、子固、莘老、微之诸作,更见酬人之情意。
夏承焘曾形容稼轩词“肝肠似火,色貌如花”。荆公性格坚硬、肝肠似火处,不下稼轩,色貌动人处亦差可比之。不过荆公强忮之处或有更甚,同时性格又有冷的一面,冷而成癖,冷至“求疵”。晚年脱去世故,那些抒发水上之思的诗作,面貌莹洁如水上之花,留给人无尽的遐思。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张亮亮
声明:久久散文网为非赢利网站,文字及图片版权均归作者所有,如相关信息侵权与违规请与本站联系,将在三个工作日内处理。
本文链接:https://www.99sanwen.com/n/121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