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爸爸的痛苦句子_失去爸爸的痛苦句子图片
- 散文精选
- 2022-03-19 04:08:05
- 115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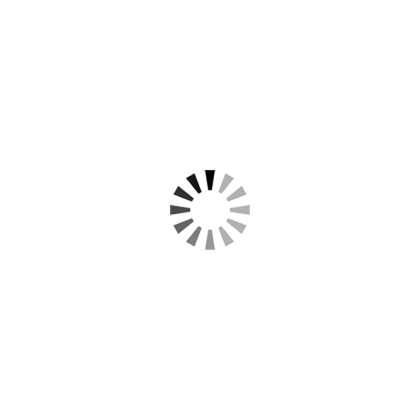
我的父亲是1948年参加革命的,享受到了离休待遇。听父亲自己讲,正式参加革命前已在村里任儿童团长三年,按有关政策应该计算工龄,找了许多部门,提供了诸多证据,最后也没接上,一直是一个莫大遗憾。我们也经常劝他,不给接就算了,怎么说您也是离休,已经够别人羡慕的了,再说离休费不是都一样嘛。父亲每次都会非常生气地说,那能一样吗?是钱的事吗?那是革命经历,国家为什么不承认?每听到这话我们便不再劝了,乖乖,“革命经历”,这个在父亲心里比天还大的词一说,大家知道,任何劝说都苍白无力。
父亲兄弟三人,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哥哥即我的大伯,比父亲大4岁,天资聪颖,上学上到北京。而视父亲和三叔愚钝,仅仅上了一两年的小学便去耪地(父亲语)。后来父亲的文化造诣连滩里中学的语文老师都敬佩有加,那都是凭借顽强的毅力自学的结果。
父亲一开始参加革命是在新镇市政府当通讯员,你没看错,是新镇市(建国前期,新镇曾短暂称为市)。通讯员的主要任务就是背着一支正规部队淘汰的破步枪步行到各村通知村干部来开会或送一些市领导们手写的文件。后来市级建制撤销后被调到文安县供销社推销科任科员。由于具备勤奋好学,忠厚老实,积极肯干三大特点,被时任推销科马科长看中,时间不长就委托一个同事作媒,将自己的三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许配给了父亲。在这期间,父亲积极要求进步,不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担任了县第三棉花加工厂的厂长,为完成全县的军需任务,支援抗美援朝做出了贡献。由于工作突出,不久被县委选派到叩里乡任驻乡指导员,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干的也是有声有色。八十年代我参加工作后,无意间在廊坊邂逅了五十年代任文安第X区(叩里所在区)区长的张庆田同志。提到我的父亲时,老区长赞不绝口,直说小伙子不错,能干事,也会干事,最大的特点是公正无私。我听后心里感到热乎乎的。在叩里工作期间,已经结婚并有了我大姐的母亲辞掉了县服装厂的工作,跟随父亲来到了这文安大洼的深处,条件十分艰苦,到后来有了哥哥,时间就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时全家借住在一个村子生产队的队部里。一明两暗的房子,人住东屋,西屋是一个没有上锁的仓库。在那个大饥荒的年代,饥饿是大家永恒的主题。大人还好说一些,可以忍着,可孩子根本没有办法忍,饿的走路都没力气。但父亲与家人约法三章,饿死也不动公家的东西。住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1962年底搬走,西屋火炕上一整囤没有脱粒的玉米棒子,愣是没少一个。十几年后我们已搬到滩里,那个村的老支部书记来看望我们,酒酣耳热之际又提起此事,老头老泪纵横,哭的像个孩子。父亲却平淡地说道,我们都是农民出身,都知道一句话,叫做“饿死爹娘,不吃种子粮”。
父亲的记忆力和母亲一样也是出类拔萃的。职业生涯中多次参加地、县党校各类培训班,平时看不到如何用功,而结业考试从来都是名列前茅。让一些使出吃奶力气还不及格的学员大惑不解。虽然文化底子浅,但对历史朝代更迭、名人掌故等耳熟能详。特别是对全县各行各业的干部尤其是老干部的家庭出身、个人履历等等烂熟于胸,每每谈起,更是如数家珍。我们有时也调侃他说,县委的领导真是缺少慧眼,绝对应该调您去组织部门工作啊,否则真的是文安县的一大损失。在几十年的基层工作中,父亲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专一行。文安大洼十年九涝,防汛工作则成了基层工作的重中之重,打堤筑坝更是家常便饭。父亲调到哪个公社都是分管这块工作,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干起来十分得心应手。文革后期,几乎每年都要带队出河工,即俗称的“上海河”,直到七十年代末。大约是八十年代中期,有几个从滩里选调到廊坊工作的天津知青听说我分配到廊坊工作,一起请我吃饭。席间你一言我一语的介绍和父亲的交往及对父亲的印象。其中一个姓陈的哥们站起来操着浓重的天津口音大声说道:“嘛也别说了,我在滩里下乡八年,跟着你父亲上了六期海河。老爷子估土方、定指标,眼比尺子都准,全工地没有不服的。我们连队年年全县第一,主要是吃的好,干的巧。最后一期换了一个人带工,全县倒数第一,他你妈根本奏不懂局。”全桌哈哈大笑,而我却湿润了眼眶。
父亲的公正无私贯穿了他的一生。有人说那时的干部什么无私啊,公正啊,都是装出来的。也许个别是存在,但父亲却绝对是骨子里带出来的,所作所为也是发自内心的。也有人说父亲“傻”,一心只想着工作,对自己对家人都没有任何额外照顾。起初我们也不理解,直到今天回头来看,父亲的品德无疑是高尚的,更是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父亲日常对请客送礼、行贿受贿、拉关系、走后门等歪风邪气深恶痛绝。文革中后期,招工、上学机会很多,因此为了走出贫穷落后的农村而送礼的也很多。小时候我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送礼人的礼品如果当场推不出去时,则由我负责送回。说实在话,我当时是非常不情愿而且很怵头的,送回去意味着不给其办事,能有好脸色看吗?多年以后母亲在我这住着时经常说一句话:“和你父亲一样的人,子女大都不是推荐上了大学就是招了工,多亏你们哥俩争气自己考出来了,不然的话肯定指望不上他,没准现在都在农村种地呢。”听后我们总是说,种地也没什么不好,搞不好还发家致富了呢?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一心一意、尽职尽责的基层干部,竟然还一度被打成了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6年夏秋之交,当时我满打满算也才三周岁,但已经有了模糊的记忆,那时我们还寄住在高头公社赖头大队。有一天突然听到大人讲,父亲是刘、邓反革命集团在高头公社的代理人之一,带头走资本主义道路,妄图让全公社广大的贫下中农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不仅停止了工作,还每天开批斗会交待问题。当时也不明白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只是看到父亲每天都很沮丧,样子也很狼狈。终于有一天父亲的精神崩溃了,身体也垮掉了,在县医院一住就是半年,母亲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父亲全部的护理工作。有一件事到今天也没想清楚,这将近两百个日日夜夜,我们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是如何熬过来的?那可是“屋外滴水成冰,屋内四面透风,缸少隔夜之米,落难即无亲朋”啊,而我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大姐当时也不过十来岁。出院后在家休养期间,仍有两个造反派头子不时到家中纠缠,动辄对父亲厉声训斥、污辱漫骂。每当这时父亲总是将我们姐弟几个护在身后,自己则倔强地昂着头轻蔑地注视着他们。而这两个凶恶丑陋的形象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然而即使是这样,父亲心中的坚定信念乃至崇高信仰丝毫也不曾动摇。每天带领我们诵读语录,自己则坚持早请示,晚汇报,雷打不动。整日为国家前途命运焦虑,为百姓饥寒冷暖忧愁。今天想来,这才应该是真正的“不忘初心”吧。若干年后,我在市里一个较大的部门负责财务工作。一次有一个很紧迫、很重要的事情有求于相关的一个单位。我们准备设宴招待这个单位的负责人,托了好几层关系,费了很大的劲才约出来。席间攀谈,我和这个负责人竟是同乡,进而深入一问,此人竟是整父亲的两个造反派头子之一的儿子,难怪这个小子在酒桌上盛气凌人、指手画脚,敢情是得到了乃父真传。我当场放下酒杯拂袖而去,留下一桌人在尴尬的气氛中凌乱,事情当然也没办成。
写到这里又想起了关于父亲的两件小事。
第一件事大约发生在1975年。父亲在本县赵王新河西码头段清淤工程工地带工,回来的民工捎信说,父亲在工地上犯了痔疮,非常严重。县医院到工地巡诊的大夫当即为其做了切除手术,目前正在卧床静养。母亲和我们听说后都很担心和着急,因此当天便和哥哥约上在大柳河供销社工作的大姐一起去工地探视。一路上我们都认为手术后一定很痛苦,估计在卧床休息。但赶到工地上找了几个帐篷也没找到。最后经人指点才在工地的中心地带看到,父亲正在和年轻的小伙子比赛推小土车呢,我们姐弟三人看了真是又着急又生气。
第二件事是我参加工作后还在单位住单身的时候,时间大约是1985年冬天。由于我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父亲总担心我不适应,或者有什么困难,因此经常来廊坊看望我。那一天父亲骑着“大铁驴”自行车从文安到廊坊,五十多岁的人一口气骑了二百多里路,到了以后天色就很晚了。记得那天晚饭我特意整了点白酒陪父亲喝了几杯,然后就早早地在我宿舍睡下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感到有些冷,睁眼一看自己躺在室外地上,头像炸裂了一样的疼,旁边站着父亲,当时感到莫名其妙。后来听父亲叙述我才明白,原来昨晚上做饭后忘记打开蜂窝煤炉子的风挡门了。父亲起的早没事就出去遛早,回来后发现我躺在屋中地上口吐白沫,当即判断我一定是中了煤气,因此立即将我拖到室外,幸无大碍。当时没什么,后来一想却感到很后怕,如果不是父亲恰巧和我一起住在一个屋里,结果可想而知。我总在想,在我生命的长河中,父亲不仅给了我第一次生命,而且还追到廊坊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有何理由不去感恩父亲?!
最令我们姐弟痛心的是,父亲年轻时身体透支严重,晚年疾病缠身。1994年,才63岁的父亲溘然长逝,永远的离开了我们。父亲的一生可以说没享过什么福,却受了不少的罪。到后来我们的日子都逐渐的好起来了,可父亲却不在了,“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我们内心深处最不能接受的地方。
声明:久久散文网为非赢利网站,文字及图片版权均归作者所有,如相关信息侵权与违规请与本站联系,将在三个工作日内处理。
本文链接:https://www.99sanwen.com/n/90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