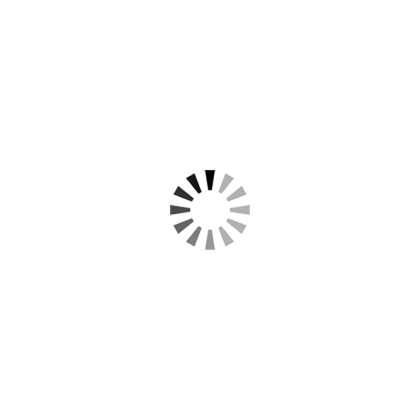洛阳纸贵的故事简短概括-洛阳纸贵的故事简短
- 生活随笔
- 2022-03-13 04:32:03
- 6623
文/吕进
今年3月20日是邹绛先生百年诞辰。
邹绛是我国著名的诗歌翻译家、诗人和诗歌教育家,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创建者之一。在研究所,方敬、邹绛、吕进一起被称为研究生的“三大导师”。1986年成立的中国新诗研究所,是新文学诞生以来的第一家独立建制的研究新诗的实体机构,也是国内外华文诗学界公认的新诗研究圣地。邹绛在这里度过了他的人生的最后10年,也是他的人生最富成果、最愉快的10年。
邹绛热爱中国新诗研究所,时时事事都挂念着研究所,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生命融进了研究所的发展事业中。我和邹绛是两辈人,但他从不以长辈自居。诗人流沙河曾经送过我一本三联书店出版的《锯齿啮痕录》,我看到了书中展现的一个有趣画面:1952年,成渝铁路在成都火车站举行通车典礼。流沙河在现场,他当年是位年轻记者。而我呢,则是在成都火车站席地而坐的川西实验小学的少先队员。戴着红领巾的我们不断地唱着:“哎——哎嗨,哎嗨,哎嗨哟,代表们哟来得早哟,我们向你问声好啊,嘿!” 邹绛,正是我们“问声好”的从重庆坐首班列车来蓉的重庆代表之一。他是195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比我的入会时间足足早了30年。但是,对我这个晚辈所长,邹绛从来理解我,尊重我,维护我,是我全天候的忠诚朋友,很给力。我们是忘年之交,并肩开路,同尝艰辛,友情很深。

邹绛与吕进(吕进 供图)
1996年1月邹绛去世后,北京《诗刊》快速地刊发了我写的悼念文章,题目是《人到无求品自高》。我在灵堂的邹绛遗像两边,挂上了我写的对联:“毕生奉献,蚕至丝尽方作罢;一世淡泊,人到无求品自高。”是的,人到无求品自高。翻译家孙法理教授是邹绛的武汉大学外语系的校友,也是邹绛的西南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同事。他写道:“邹绛是我的老学长,一起工作的时间很多,却从没有听见他发过一句牢骚。我曾经对学生说他是个圣人,学生也有同感。”
邹绛声名远播。他就是一部外国诗歌的活辞典,精通英语和俄语。中国许多读者都是通过他,才认识智利诗人聂鲁达、美国黑人诗歌和俄罗斯诗人巴格里茨基的。他还是新时期格律体新诗有影响的倡导者,在诗体重建上多有贡献。他去世后,诗人张继楼曾给中国新诗研究所送来一幅挽联:“ABCD随风去,平仄对仗留人间”,十分准确地概括了邹绛的成就。
邹绛是学术权威,长期担任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外国文学研究会的会长,但他虚怀若谷。从1983年到1992年,重庆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邹绛主编的4卷本《外国名家诗选》,一时洛阳纸贵,实现了邹绛编出“一部丰富多彩而又耐读的诗选”的预想,我翻译的俄罗斯诗人伊萨可夫斯基的几首诗也荣幸地被他编入。著名诗歌翻译家王佐良先生把这套“诗选”列在“外国文学阅读书目”的“诗歌类”之首,这当然是很高的评价了,但是,我却从没听他自己说起过这事。有一位现在已是中山大学教授的西南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生,当年的两首译诗,是邹绛一手帮他改的,因此在收入《外国名家诗选》时,他郑重地将邹绛列为第一译者。书出来后,他一看,邹绛已经把自己的名字删掉了。
邹绛是一个淡泊的人,低调的人,几乎从不谈论自己。有一次,我到他家去谈工作,在他打开书桌抽屉翻找我需要的资料时,我偶然看到抽屉里有一封胡乔木给他的亲笔信。我立即取出来,抽出信笺阅读。胡乔木写得很热情,对邹绛倡导的现代格律诗赞许有加。胡乔木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之一,且具学者身份,读书较多,发言慎重,他明确支持邹绛的努力,这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啊。邹绛却以寻常心对待,把这封信雪藏了。如果不是我的偶然发现,谁也不知道有这回事。
邹绛西去后,他的姐姐邹德鸾女士给我写来一封长长的信,一共有6页。邹德鸾比邹绛长6岁,在信里,她简短地回顾了弟弟的一生,也叙述了弟弟对新诗研究所的深情。读了德鸾女士的信,我才更详细地知道了邹绛的人生道路。邹绛本名邹德鸿,因为追求革命,以“邹绛”为笔名。绛者,红色也。当年为了躲避他的家乡四川乐山的反动当局的追捕,来到了重庆。邹绛是“革命军马前卒”邹容的侄子,民盟盟员,在1949年以前就和中共地下党时有接触。1947年,邹绛接待了母校武汉大学地下党介绍前来的一位党员,来人不是别人,正是小说《红岩》写到的江姐。
邹绛给自己树立的人生标杆很高,他是一个完全没有低级趣味的脱俗的人,纯净的人。他的境界很高,“吃的是草。吐的是奶。”时间也许可以划分为无价值时间和有价值时间,可以说,邹绛的时间全部是有价值的时间。他在诗的世界繁忙,对诗外世界的一切不愿花时间去关心。住的是一间没有厨房、没有厕所的小房间,一日三餐都拿着饭盒去学校食堂打饭。1987年,学校评审高级职称的时候,人事处长老宋给我打来电话说,这次教授名额不够,邹绛就评研究员吧。他说,研究员的任职条件其实比教授更高,但一些人不了解,总是更愿意评教授,“请你这位所长务必抽时间亲自上门,做好邹老师的工作。”我自然心中有数:这等“俗事”,何须上门啊!我打电话给邹绛,说了情况,他只“啊”了一声,就转过来谈编辑新诗研究所的所刊《中外诗歌研究》的一些事情了。考虑到邹绛从来没有出过境,我便向境外的大学推荐邹绛,他很高兴,但又反而来规劝我:“老吕,出去的事都不要考虑我,我手头还有好多事要做啊!”这是一种多么耀眼的光亮啊!
他住进医院以后,我只要去探视,病房就等于开起了工作讨论会,研究生啊,学术梯队啊,当然更多的是《中外诗歌研究》。在弥留之际,他还在病床上向教学秘书小李口述研究生期终考试的考题。当夜,他就离开了我们。诗人梁上泉曾经有一首写邹绛的诗,有“生死是吾师”之句,也道出了我的心声。
对名利满不在乎的邹绛却是外圆内方的。他诚挚宽厚,但他是非分明,对于不择手段满足一己私欲的人,表示出了很大的鄙视。我记忆中很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那时,西南师范大学被驱赶出重庆,迁到梁平县的一所中学里。我和邹绛都发表过文学作品,所以都是与文艺黑线有关联的“有问题”的人,被集中关在一间单独的小房子里,便于看管。房子外面有个水缸,是全系教师的饮水,晚上由人轮班值守。我发现,已经开始第三遍轮值了,仍然没有叫过我和邹绛。我找负责人抗议:“你们是不是怕我们要在水里投毒?”于是我们也值班了。我很得意,但我却第一次听见邹绛抱怨:“十冬腊月的,这么冷,争什么值班嘛。”我说:“这可是群众的资格啊!”他苦笑:“哎呀,别理他们那一套。”大有“看庭前花开花落,观天上云卷云舒”的气概。
在邹绛先生百年诞辰前夕,重庆出版社及时推出了新诗研究所编撰的《邹绛诗文集》。纪念活动的消息发出后,要求到会的来函很多。新诗研究所所长向天渊教授给我发来微信说:“吕老师,人很多,看来要换更大一些的会场才行。”其实,原来安排的会场,是北温泉公园的数帆楼,既是名楼,又是中国新诗创研中心的活动场地,已经不小了。看来,邹绛没有远去,这位“人到无求品自高”的“圣人”永远令人感到亲切,永远让后人景仰。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欢迎向我们报料,一经采纳有费用酬谢。报料微信关注:ihxdsb,报料QQ:3386405712】
声明:久久散文网为非赢利网站,文字及图片版权均归作者所有,如相关信息侵权与违规请与本站联系,将在三个工作日内处理。
本文链接:https://www.99sanwen.com/n/49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