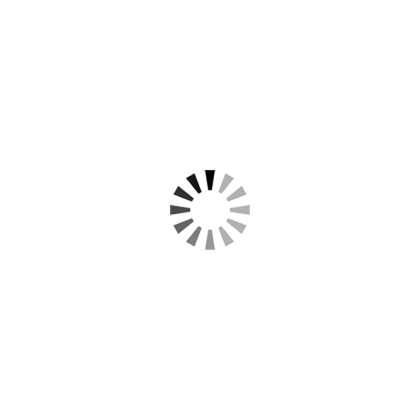养虺成蛇是什么意思_水虺现实是什么蛇
- 杂文
- 2022-03-30 19:24:23
- 7436

故事:边境连失七城,满朝哗然,二十岁的她请缨道“愿替父出征”(上)
这其中自然少不了宁宿的功劳。
一晃经年,宁宿的眉眼也多少刻下了被边塞磋磨的痕迹。他学会了痛饮庆功的酒,学会了围绕篝火高唱,学会了在刀山箭雨里享受疏狂肆意,还跟廖莘学会了骑马。
一次喝醉,他竟如卫及一般伸手勾住了廖莘的脖子,两双迷蒙醉眼对视,在星光灿烂中碰撞出一抹绚烂非凡的亮色。
廖莘顶着脸上两坨晕红笑道:“先生醉了。”
醉了,他也知自己有些醉了,却是越醉越清醒,平时压抑在心底的某些东西趁机越狱出来,催使他吻上廖莘的唇,二人交换着嘴中的酒气,廖莘蓦然惊醒,并不反抗,直至宁宿的唇离开。
“都不如你……上古宝琴,天命劫数,什么都不如你。”
言语切切,她却望见他神色迷蒙,似乎比方才醉了许多,半疯半癫、摇摇晃晃地走回自己的营帐,让她摸不准他是真醉假醉。
翌日醒来,廖莘斗胆去给宁宿请早安,宁宿正在擦琴,看她的目光与以往无半分不同,似乎完全忘记昨夜发生过什么。廖莘不禁怀疑昨夜到底是谁醉了,又是谁做了一个难以言说的迷梦。
他的怜爱依旧全然放在琴上,开口漠漠问她:“将军找我何事?”
廖莘不露悲喜,同往常一样对他恭敬道:“廖莘想请先生同去逛一逛丰城。”
繁荣似梦,满城风絮,廖莘身着一袭轻纱行走在宁宿身旁,恰如他当年第一次见到她一般。
这些年,他悉心调养她的身体,尽量使她那些战伤不留下伤疤,而今青丝微绾,莲步徐徐,睹不见无情战事给她划下的那些痕迹,谁还能看出这就是那位战功赫赫的女将军?
连此时此刻走在她身边的宁宿,都险些忘了。待江山平定,这般女子又该何去何从?又会是怎样的人物,才能与荣光无限的她比肩而立?
至少,不会是他。青衣书生,只有山中归处。
“昨夜卫及禀报,说是发现了藏匿的喀尔克及其余部,几年短暂太平,是时候解决这最后一支残余势力了,绝不能等到养虺成蛇。”
他轻摇一把折扇,仍然目视前方,“无论将军决定什么,宁某都会追随。”
远在边塞的州城里居然会出现江南的苏绣织品,廖莘捏起那帕子,心中腾起万千感慨。“最后一场仗了,此战过后,先生有何打算?”
他伫足于那苏绣摊子前,与她侧身而立,彼此不见神情。风絮漫天,终于换得他一声呢喃:“自然是回到乾清山去,想来将军也没忘记承诺。”
她当然没有忘记,可是时光荏苒,她始终不愿相信,他会守着一个执念三年不变。
廖莘愈发地怀念江南,怀念它的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8
祭酒洒地,告知家翁,愿先天之灵保佑此战必胜,大祁万世太平。
十里草盛没过脚踝,祭拜完的廖莘擦过宁宿身边,对他道了句“走罢”。宁宿跟在她的身后轻声允诺:“将军放心,此役宁某定助将军得胜。”
“我知道。”她回答。
自从有他陪伴在身边,廖莘从来没有不放心过。此役不过是剿灭一股余军,远不及过往某些战役凶险,只因这场仗的胜利意味着西境彻底安定,所以她才要祭告亡父,同时也是在与自己的戎马生涯提前道别。
自此以后,她笑看她的万世太平,他独享他的山间逍遥。如此一想,方才道别的应不只是戎马生涯。
回营研讨战术,却发现喀尔克所藏匿的深林神秘莫测,而今恰是草木繁茂之季,廖莘等人不知其中情形,故而对方占据地利,此战并不如先前所想的那般简单。
关于是否涉险入林,诸人叽叽喳喳争论许久,廖莘望向竟然一言不发的宁宿,问道:“先生有何看法?”
“入。”他放下茶盏,走过去指着地势图,利用自己所学帮众人分辨何处是沼泽、何处是水林、何处有瘴气、何处生毒草。
言罢底下一众鸦雀无声,人们怀疑他对环境的判断是否可信,同时又顾虑于廖莘对他的尊敬,故而唯有沉默。
宁宿转而问向廖莘:“将军看来如何?”
“不经勘察,先生可有把握?”
“宁某说过,会助将军此战功成,就一定言而有信。”
廖莘遂对众人下令,决定明日入林剿敌。
诸人退散后,宁宿独自找到卫及,将一件重要的事交代给他。回帐时,大雁掠过,数声啼鸣,他又想起师父的那句预言。
同样为预言所困的不止他,还有师父,师父为了躲避劫数佯装离世,实则藏在山中隐逸不出。
来客一遍遍叩响山门,他和师父坐在里面品茗不理,可门外的人似乎立了天大的决心,终于一天他忍不住问:“若徒儿出山,尚有几年活日?”
得到告知:“不出四年。”
答应出山襄助廖莘当夜,师父执意阻拦,言说天机不可违,违者必无善终。他却反问:“师父可知我为何不学窥探天机?”
良久自答:“因为我不信天机,只因人谋。”
山林无路,众人只得下马步行,按照宁宿所标注的地图前进。直至夜临,都不曾见到过敌军踪影,军队里开始出现质疑声,毕竟眼下无论是回去还是继续行进都是安危难测。
宁宿始终抿紧双唇,攥着火把在前方引路。
喀尔克深知只要离开林子便会毫无迎击之力,唯有倚赖地利才有以少胜多的可能,自然不肯轻易出现,从进入林子里那一刻起,祁军便已处于被动。
可他实在没有时间在外死等了,西蛮人生于长于此地,自然适应等得住,倘若哪天寻到秘径悄悄出去东山再起,廖莘心血便付之东流了。
他必须放手一搏,哪怕身后诸人皆不信任。
廖莘忽然叫住他,语气里透露出从未有过的提防:“先生,我们可是踏入了敌军的包围?”
一路蛛丝马迹,皆是人为布置的痕迹,她信他,所以一路跟随至此。可眼下她需要他给出一个解释,不为给她,也得给身后的随军。远处忽然亮起隐隐火光,显然是喀尔克余部的火把。祁军顿时摆出防备的队形,廖莘横眉怒目道:“先生!”
却瞬间眼前一黑不省人事。
地形原因,喀尔克军队只能形成一个半包围圈,逼得祁军只可往里行进,无法后退。天色已然漆黑,喀尔克等人险些就追丢了,幸而一曲琴声悠荡,指引他们循声找去。
然而,声源处唯一人一琴而已。喀尔克环视一圈,对青衣书生凶狠道:“廖莘何在?”
“她不在。”嘴角噙着笑意,仿佛再自在不过。
喀尔克不信,一刀横在宁宿颈上,“廖莘才不会舍下你这宝贝军师呢,她一定就在你周围!”
“你错了。”琴音弹罢,宁宿抬首直视喀尔克双眼,“她从不需要依赖任何人。”
9
廖莘醒来的时候,得知了喀尔克余部被剿的消息。
置之死地而后生——宁宿的另一个手笔,只有他和卫及知晓。
是卫及将廖莘弄晕的,然后由宁宿孤身引喀尔克反入卫及所设的包围圈,才有了这场得之不易的胜仗,才有了大祁此后的太平盛世。
喀尔克及寥寥存活的西蛮士兵被活捉,宁宿却不知所踪。
“说出宁宿下落,我饶你们不死。”
喀尔克看出廖莘的软肋,讨价还价道:“我还要丰城。”
廖莘暗暗咬牙,攥紧拳头,恨不得一口啐在他脸上,骂他休想,可自己一句话便动及宁宿性命,她唯有隐忍沉默。卫及请求将喀尔克交给他审问,承诺必定问出宁宿下落。既然她难以抉择,那么就让他替她去选吧。
廖莘未解甲胄,只是坐在营帐里擦拭宁宿钟爱的琴,一言不发。湿布触碰到溅上血的弦,奏出来不成调的悲鸣,恰如她此刻忐忑不安的心跳声。
琴上的血是谁的?宁宿的,还是别人的?
廖莘不敢细想下去,闭了眼睛,将手中的湿布紧攥成团。这时卫及进来禀报:“将军,敌军残部已被悉数剿杀。”
“什么!”听闻卫及自作主张,廖莘猛然站起,一掌拍得桌案响亮,“那宁先生呢?”
卫及慌忙跪下,安抚她说:“将军安心,宁先生已经回乾清山了。他说,答应将军的事已经做完,此后将避世不出。”说罢,又呈出宁宿的道别信。
廖莘缓缓坐回原处,怔怔道:“也好。”
总算是如了他的心意,往后余生,只有梅妻鹤子,再无刀光剑影。廖莘盯着面前的琴,心中却隐隐觉得有股失落。
可,尘世里就丝毫没有值得他留恋的东西吗……
等等,这不是宁宿的笔迹,而是卫及的笔迹!
“卫及,你骗我?”
“这确实是属下代笔的。”卫及闭着眼睛说,“因为……先生的手指被喀尔克砍了。”
西蛮境军全线溃败,西境军长驱直入,一口气连占对方十余州城,眼见就要将整个西蛮吞并。西蛮君主立刻命使臣带来乞降书,以割让十座城池及每年进贡为条件,换取大祁庇护,以后西蛮就是大祁的附属国,再不进犯。边境连失七城满朝哗然,二十岁的她请缨“愿替父出征”。
这封乞降书给大祁朝堂带来争议,多数朝臣认为,只要大祁坚持攻打下去,西蛮定是大祁的囊中之物,岂可因为一点蝇头小利就错失不二良机。首辅陈满却认为,数年战乱已使边境民不聊生,及时止战方是王道。
老皇帝遣人去询问廖莘的意见,廖莘望着一旁的古琴,独自低喃:“若你在,定不想再看到生灵涂炭吧。”
于是拟了支持停战的奏表,托差使带回京师。次年四月,两国签订隶国书,书中写明:西蛮此后为大祁属国,裁国内一半兵力,两国边境由大祁驻军戍守,西蛮每年向大祁上贡良驹、金矿石和蚕丝等物。
西境边务皆交由廖莘掌控,她下令两国可在交界州城自由互市,短短两年时间,这片被鲜血渗透的不毛之地变成了太平乐土,人间烟火令人们忘记了这里曾经发生过数年杀戮。
闲时,廖莘总喜欢身穿一袭轻纱走在闹市中,无人认出她正是给这片土地带回安宁的那位将军。
她守着宁宿留下的琴,从不通音律到熟识琴韵,用了两年时间。每当她在弦上落指,一腔孤勇就会化成柔情似水,廖莘才会想起自己尚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姑娘,想起自己偶尔也需要肩膀靠一靠。
这一年,老皇帝病重不起,除召见太子交托后事之外,就只召了廖莘一人回京述职。
廖莘跪在床前攥住老皇帝的手,像是女儿见到了父亲。老皇帝欣慰一笑,有气无力道:“朕终于可以去见世忠了。趁朕还有一口气,你可有什么愿望想实现?”
廖莘笑得温柔,“陛下,臣就是有点累了。”
老皇帝的最后一道旨意,是让卫及替任西境军主将一职,并封廖莘为荣国公主,位同长公主。
新皇登基的角声悠荡在整座宫城,大祁迎来新的年号:靖忠。
10
柏木大门轻轻叩出三个响儿,长高许多的童子从门里钻出来,对廖莘说:“先生不见您,荣国公主以后不必再来了。”
廖莘怀抱古琴,长睫未颤,“廖莘不奢求先生宽宥,只是想送回先生的旧物。”
世道太平后,她似乎只剩这一件事可做,然而无论她来了多少次,宁宿总是不见。乾清山一切照旧,世事几番变迁都不曾影响到这里,谁不乐于在此处度过一生呢?
“先生说十指已断,不需此琴了。”
柏木大门无情合上,独留一人一琴在山道上的落寞身影,廖莘的低喃被吹散在山风里,无人知晓。
“当真不要你的妻了么……”
三十年后,年逾五十的廖莘旧疾发作,沉疴难医,须发皆白的卫及闻讯从西境快马赶回。行将就木之际,她拉着卫及的手说:“我只有一件事放不下,你去替我求求宁宿,让我能看他一眼。”
卫及顿时老泪纵横,告知实情:“宁先生已经先您而去了。”
“何时的事情……”
“三十年前。”
尘封久远的秘密终于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大白,原来不是不见,更不是怪怨。三十年前,三十年前,廖莘盯着床顶回顾起三十年前的场景——
骏马长枪,战旗铮铮,一个青衣书生手抚古琴,摆布天下。
当她躺在床上垂垂老矣的时候,他永远留在了最风姿俊逸的年纪,永远地沉睡在那片沼泽林地里。
廖莘临终释然一笑。也好,又能听先生弹琴了。
史书有名,青山无冢。靖忠三十一年,荣国公主病逝,西境十里白绸轻扬,只为祭奠那个为万世开太平的女将军,和她逝去不回的戎马时光。(作品名:《荣国女将》,作者:婴心。来自:每天读点故事APP,禁止转载)
点击屏幕右上【关注】按钮,第一时间看更多精彩故事。
声明:久久散文网为非赢利网站,文字及图片版权均归作者所有,如相关信息侵权与违规请与本站联系,将在三个工作日内处理。
本文链接:https://www.99sanwen.com/n/169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