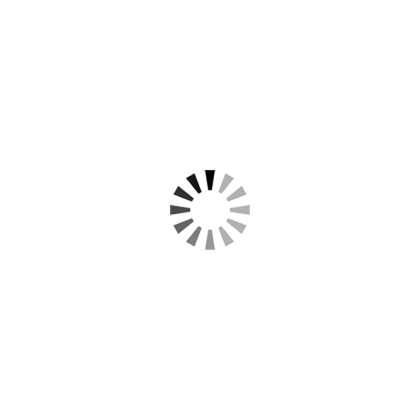宣传眼镜最有力度的广告短语(关于眼镜的宣传广告)
- 杂文
- 2022-03-26 18:26:07
- 6838

互联网世界,有一群隐秘的工人。
他们躲在社交媒体创造的巨量内容之后——平均每分钟,世界最大视频分享平台就会上传69万小时的视频、世界最大社交媒体“脸书”有24万多张图像被分享(引自云软件公司DOMO最新发布的Data Never Sleeps 9.0报告)。
每天,数百万人不分国度、不分昼夜地擦拭我们的线上世界,处理点赞、评论、话题刷屏、流量“爆款”等一系列事务,但我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这群人重复着简单、枯燥的工作,因此被形象地称为“点击工人”,别称则有“鉴黄师”“数据工”“投饵人”等。
不被看见的人群
艺术家马丁·勒·舍瓦利耶是在报刊、网络上发现这群点击工人的。他们在网络世界无处不在,但在现实中却近乎“隐形”,绝大多数人都在几平方米的房间里工作。
为此,马丁拍摄的电影《点击工人》(Clickworkers)中,没有一个人露脸,一个房间就代表一个人物——这是对点击工人身份的巧妙隐喻。
“叮”一声,来任务了。李莉不管手头正在忙什么——给孩子喂奶或半夜睡觉,她都要第一时间赶到电脑前。她需要在几分钟内处理一批任务,否则,她很可能失去这份工作。
这份工作要求随时随地响应。许多跟李莉一样的点击工,都会将闹钟定在半夜起床。夜里干活,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处理的工作并不复杂,但一定要细致。李莉通常会在网上创建一堆小号,以便批量出售“粉丝量”。有时,她也会出售观看量等,“点开一段视频,停几秒,然后关掉”——她重复过无数遍这样的动作,但她从来不看这些视频。
很多时候,点击工人不知道这些工作的真正用途,甚至不清楚别人为什么要找他们。他们只是流水线的一环,把最简单的动作重复、重复,再重复。
其他类型的点击工人,正如电影《点击工人》描述的角色那样:标签员负责给一系列图片贴上诸如色情、暴力、恐怖主义等标签,以便它们被进一步审核,最终决定它们“删除或保留”;数据工往往有一个小团队,通常一个人管理好几百个账户,他们批量销售点赞量、观看量,几乎所有时间都用来点赞;转录员负责将所有的视频、音频乃至账单等,转成书面文字;数据标注师则专门训练人工智能。
尤为特别的,是评论员这个角色。他们经常闷在家里,想象自己从没去过的餐厅、酒店、旅游目的地。任务里的名词总是换来换去,但他们评论的话术基本不必更换,必须是正向的,如“味道超正”“特别舒服”“太赞了”……
总而言之,这些工作都相对简单、重复且枯燥。但矛盾的是,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简称ILO)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这些点击工人通常有着相当不错的教育背景——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有学士学位,五分之一的人拥有研究生学位,往往熟练掌握至少两国语言。
在中国,不少名校毕业生和归国留学生会把内容审查员等岗位当成挤进“大厂”的敲门砖。
但事实上,ILO报告指出,很多点击工人往往服务于第三方外包公司,更像临时工,享受不了公司的任何福利保障。
他们一天要工作十几二十个小时,一周至少工作6天,却拿着很低的薪水。国外的点击工平均时薪为4.43美元,大多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在国内,这些人月薪大多是五六千元——对比他们的工作量,算不了什么。
当代“殉道者”
坐在赛车机上,玩几把游戏,把精力消耗掉,是一名内容审查员(以下简称“审查员”)难得的宣泄自我的方式。审查员是极为特殊的点击工人,也被称为“鉴黄师”。
他们面临的是夹杂着恐怖主义、色情与暴力等内容的更真实的互联网世界——他们的任务就是筛选这些内容,防止网友们被屏幕前突如其来的怪东西吓坏。他们了解一切与色情有关的用具、用语,甚至熟记恐怖主义的口号、旗帜,等等。
删除或保留,是他们工作的全部。此外,他们什么都做不了。
在汉斯·布洛克导演的纪录片《网络审查员》中,有一个令人惊愕的细节:一名审查员潜入直播间,播主正试图将自己的脑袋套上绳索,努力蹬开椅子,身子就像木偶一样挂着。但审查员什么都做不了,他没法阻止、没法劝说,只能跟直播间的上千人一起目睹了这一切。
面对一张图片或一段视频,审查员只有几十秒的考虑时间。一名来自菲律宾的资深审查员,一天就要面临两万多次这样的抉择。
相比之下,他们的容错率非常低。“脸书”的前审查员公开表示:“你每个月最多只能犯四五个错误——2%的失败率和98%的质量分数。”
久而久之,审查员的内心会像“塞满了脏东西的下水道”一样,很难找到排泄的出口。
审查员须签署保密协议,不能跟任何人透露与工作相关的内容。就连希望公司提供一间可以自我放松的游戏室,对绝大多数审查员来说都是奢望。更多时候,他们只能自救——捏碎一包方便面、吃大量零食,或者大汗淋漓地玩一场球等。但这些措施,属于治标不治本。
艺术家劳伦·于雷特地去菲律宾寻找这些审查员。由于拥有大量精通英语的廉价劳动力,长期以来,菲律宾是美国社交媒体巨头主要的内容审核外包公司所在地。“他们处理的‘内容垃圾’,大部分来自美国,这本身是一场新殖民主义。”于雷说。
于雷了解到,很多新审查员不出几个月就会出现精神抑郁的状况。对“脸书”提出诉讼的审查员克里斯·格雷,就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是审查员极其容易出现的一种病症。
《网络审查员》中,一位被安排审查“自残”直播的审查员,因此产生了自杀倾向。目前为止,所有审查员面临的心理问题都不受重视,也没什么行之有效的解决措施。
不过,于雷发现,那些长期工作的菲律宾审查员往往将自己的工作“崇高化”,将删除那些“肮脏”图像视为一种“救赎”。《网络审查员》中,一名审查员表示:“我不想引起关注,我们的工作就像警察。和现实世界一样,必须有人来守护。”另一名审查员则表示:“我蛮喜欢这份工作的,很有成就感。”
于雷将这些审查员称作当代“殉道者”,为了守护数十亿人,他们不惜独自承受那一切肮脏的内容。
为此,于雷在自己创作的反映菲律宾女审查员的图像装置旁,放了一幅圣母玛利亚的人像。“圣母玛利亚代表着历经苦难同时备受尊敬的女性形象”,这是对审查员身份的隐喻。最终,于雷将这件作品命名为《为我的仇恨者祈祷》(Praying for My Haters)。

红砖美术馆“图像超市”展览现场。艺术家劳伦·于雷的作品《护眼符》与《圣路济亚肖像(莱斯莉·安-曹)》。
“把人脑当电脑用”
把脑袋努力凑近屏幕,截取视频的某一帧并放大,对每一处脸部特征、骨骼弯曲点进行标注——这是一个数据标注师(以下简称“标注师”)每天面对的工作。
这项任务,是人脸识别的重要步骤之一。人工智能并不是生来就能识别人的五官,它需要海量的训练。
类似的标注师工作还包括“用电脑摄像头录制40个在空中画数字的视频”“你的浏览器记录了几个短语”等,这一切,都是为了辅助“机器学习”。
这些工作技术含量并不高,但难在精准度一定要高,一个动作要重复成千上万次。
“稍有偏差就会产生错误,一张图有错,有时会影响整个数据包的数据,然后整个‘回炉重造’。”一名标注师表示,“这行干久了之后,我清楚地知道客户要通过我们实现什么——就是把人脑当电脑用。”
标注师的工作是为了训练人工智能,但吊诡的是,训练人工智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替代这些标注师。这是一项注定会被抛弃的工作,就像日抛型隐形眼镜一样,用过就可以丢掉了。
不仅是标注师,几乎所有点击工人都很难摆脱被抛弃的命运。ILO报告提到,很多“点击工种”的诞生,源于人工智能的“失败”,“无法满足互联网公司寻求扩大他们可以在网上存储、分类和提供的数据领域的需求”。
当需求激增时,这些劳动力就被填补进这个市场,变成一台台“人工智能”。他们可以随时填补,也随时会被抛弃。
ILO报告显示,点击工人对目前的工作普遍抱有强烈的不安全感,看不到这份职业的未来。
但整个市场对点击工人的需求还在持续上涨。最近,“脸书”还在扩招自己的内容审查员。
据外媒Vice报道,“脸书”已将大部分内容审核外包给了15000多家公司,整个内容审核团队人数超过几万人。不久前,阿里巴巴发布了“日薪1000元,AI鉴黄一日体验官”的招募令。
2021年9月1日起,我国《数据安全法》正式施行。严监管下,市场对内容审核的需求进一步扩大,一些内容审查的创业公司陆续涌现。
或许,对点击工种的旺盛需求,还将催生一个互联网新风口。
但别忘了,本质上,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剥削——源头是社交媒体时代不加节制生产的过剩内容。而过剩内容越多,剥削越发加重。
声明:久久散文网为非赢利网站,文字及图片版权均归作者所有,如相关信息侵权与违规请与本站联系,将在三个工作日内处理。
本文链接:https://www.99sanwen.com/n/141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