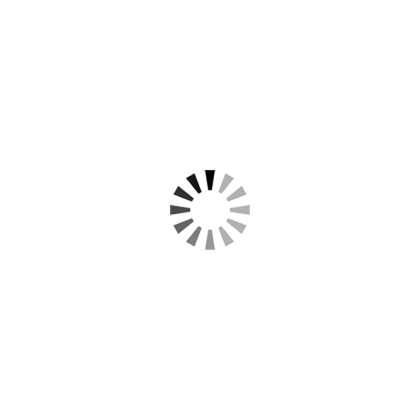细读呼兰河传读后感(呼兰河传读后感50字左右)
- 杂文
- 2022-03-25 20:52:04
- 5892
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师范大学张莉教授的最新散文随笔集《小说风景》。
《小说风景》中分析的大多是读者已耳熟能详的篇目,张莉旨在以“重读”探索作家们的成长和革新之路,思考他们如何在百年文学传统的脉络里确立自我风格。通过文本细读,张莉也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所关注的核心命题:白话小说传统、文体革命、爱情话语的变迁、中国民族风格的构建、革命抒情美学的形成等。
关于自己的批评观,张莉在书中谈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批评形成了新模式,批评者借用某种理论去解读作品——西方理论成了很多批评家解读作品的“拐杖”,甚至是“权杖”。另一种模式是,批评家把文本当作“社会材料”去分析,不关心作品本身的文学性,不注重自己作为读者的感受力。张莉谈及:“我不反对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也不反对研究者对理论的学习与化用,我反对教条主义。这使阐释文学作品的工作变成阐释‘社会材料’的工作,进而这种隐蔽的教条主义形成了可怕的从社会意义出发阐发作品的阅读批评习惯——一部作品是否具有可讨论的‘文学性’,是否真的打动了你完全被人忽略。”
因此,张莉认为,在文学批评中,人的情感和人的感受性是重要的,在批评领域,在占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人的主体性应该受到重视。文学批评不能只满足于给予读者新的信息、重新表述前人的思想,它还应该反映作者的脑力素质,应该具有对文本进行探秘的勇气与潜能。
这种批评观念也贯穿于张莉的教学中。近三年,张莉在北京师范大学给研究生开设“原典导读”课,与研究生们一起共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她说“我听过年轻人在课堂上的热烈讨论,我也曾向他们讲述过我的诸多理解,我甚至觉得,那些美妙的时刻也意味着这些文本早已不仅是文学史深处的文本,它们也勾连起了我们当下的生存,进而建立起我们与他们、当下与历史的情感联结。换言之,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文学实践,建立一种属于我们时代的‘文学的读法’。”
《小说风景》也是张莉批评观的具体实践,在书中,张莉对于不同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从“建立情感连接”的角度做出如下评价:
“郁达夫作品的主题,最饶有意味的地方在于不是写‘性’而是写‘情’,对于这位作家而言,重要的不是认出故人、认出情人,而是认出同类;重要的是作为受苦人遇到受苦人,作为失意人遇到失意人。”
“萧红《呼兰河传》里,即使是最庸常的民众身上,也有着令人惊异的活下去的能量。萧红对于呼兰河人民的生存,既有五四启蒙思想的观照,也有站在本地人内部视角的认知,甚而,她有着对人类整体生存的认识:呼兰人的生存里,既有人的无奈、人的苟且,也有人的超拔。”她写下对于革命抒情作品的理解:“孙犁以个人声音写出千万人的心之所向,由此,‘个我’便也成为了‘公我’,‘个我’与‘公我’情感与价值取向的高度契合是优秀革命抒情作品成功的关键。”
作为一位持续关注女性文学领域的专家,张莉对于一些文学作品也有新的解读视角,如解读鲁迅的《祝福》时,她观察到小说中女人们对祥林嫂的指责,在她看来,“柳妈之所以能占领这个居高临下的位置,可以站在审判他人的角度,在于祥林嫂和她都相信女人节烈这一话语体系。”她谈何以是女性之美?“某种意义上,铁凝重新发现了女性身体之美,她将女性身体从外化的标签中解放出来。这些身体不是供欲望化观看的,但也不是用来展览的,铁凝笔下女性之美,是对自我身体的凝视、认同、接纳,是自信与自在,是以健康和强壮为底的。”
关于书名“小说风景”,张莉认为,每一部优秀小说、每一个经典文本都有它独一无二的风景,都有着它隐秘的入口,需要读者去发现。福柯曾说:“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它把火点燃,观察青草的生长,聆听风的声音,在微风中接住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它增加存在的符号,而不是去评判;它召唤这些符号,把它们从沉睡中唤醒。也许有时候它也把它们创造出来——那样会更好。下判决的那种批评让我昏昏欲睡。我喜欢批评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它不应该是穿着红袍的君主。它应该裹挟着风暴和闪电。”
“今天是视听化的时代,我们的生活已经被短视频所充斥。但是,阅读依然有着它不可替代的美好——今天的我,越来越喜爱重读,也越来越流连于百年中国故事中的薪火,越来越喜欢从那些历史中的文本去体察新的美与愉悦,进而重新认识我们当下的文学生活。”张莉谈道。

附《小说风景》选摘:
一个女人的“逃跑”与“自救”
《祝福》结构工整,开头和结尾呼应。开头是一个辞旧迎新的场景。“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这是我们常见到的春节景象。这是理解这部小说非常重要的背景。春节的气氛中,小说写到三次下雪,而这三次下雪,与叙述人回忆祥林嫂的一生是相互映衬的。几乎所有研究者都不会忽略“我”与祥林嫂的对话。这是祥林嫂第一次出现在文本中,也是非常经典的片断,那应该视作“我”与祥林嫂的劈面相逢。
那是下午,我到镇的东头访过一个朋友,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见她;而且见她瞪着的眼睛的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两个人见面了,怎么开口呢?小说这样写道:
我就站住,豫备她来讨钱。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这是小说中的第一个小高潮。一个“纯乎乞丐”的女人问出了一个非常有精神高度的问题:“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她没有得到回答。而就在叙述人也觉得迷惑的时候,更大的震惊感马上到来,祥林嫂死了,并且被鲁四老爷指斥为“谬种”。至于怎么死的,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想提起,“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这句无情的、充满鄙夷的回答,立刻让人觉出祥林嫂命运的卑微。就在这样的回答之后,仿佛在回应“穷死的”这个说法,小说有一段抒情、伤怀但又很美的段落。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人们都在灯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静。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瑟瑟有声,使人更加感得沉寂。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
在悲哀、寂寥又不无反讽的语句里,我们看到了祥林嫂的前史。最初,她是健壮的、有活力的女人。“她不是鲁镇人。有一年的冬初,四叔家里要换女工,做中人的卫老婆子带她进来了,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但是,她很快被捉回,被逼着远嫁。命运发生逆转,第二次见时,“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而第三次呢,“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生命的活力从祥林嫂身上消失,她越来越苍白,越来越失神,直至变成“行尸走肉”。诸多研究者都论述过祥林嫂的受害和她命运的被动性。但是,她真的只是一个完全被动的承受者吗?
进入文本内部,站在祥林嫂的角度,我们会看到她不是束手就擒的人,她一直在反抗,一直在努力争取命运的自主权。《祝福》中固然可以看到鲁镇环境对祥林嫂的种种压迫,但也要看到一个女人的拼命挣扎,而正是压迫与挣扎所产生的巨大张力和碰撞,小说才有了一种内在的紧张感。
事实上,小说中给出了她第一次出门来做用人是逃出来的信息,这样的“瞒”与“逃”,便是这个女人的反抗。所以,也就是说,小说给出的第一次反抗便是逃离婆家,到鲁四老爷家来打工。这并非想当然,小说中有明确的信息:
新年才过,她从河边淘米回来时,忽而失了色,说刚才远远地看见一个男人在对岸徘徊,很像夫家的堂伯,恐怕是正为寻她而来的。四婶很惊疑,打听底细,她又不说。四叔一知道,就皱一皱眉,道:
“这不好。恐怕她是逃出来的。”
她诚然是逃出来的,不多久,这推想就证实了。
“她诚然是逃出来的”,“逃”到鲁四老爷家是祥林嫂的第一次反抗,而顺着这个路径,我们可以爬梳出小说内部祥林嫂反抗的整个时间线。第一次逃出来,被人捉回去再嫁,于是有了她第二次反抗。
看见的人报告说,河里面上午就泊了一只白篷船,篷是全盖起来的,不知道什么人在里面,但事前也没有人去理会他。待到祥林嫂出来淘米,刚刚要跪下去,那船里便突然跳出两个男人来,像是山里人,一个抱住她,一个帮着,拖进船去了。祥林嫂还哭喊了几声,此后便再没有什么声息,大约给用什么堵住了罢。接着就走上两个女人来,一个不认识,一个就是卫婆子。窥探舱里不很分明,她像是捆了躺在船板上。
第二次反抗,哭喊过,后来被拖进船里,“捆了躺在船板上。”此时,她被当作一种交换物,直接卖到了山里。第三次反抗,从卫婆子的叙述中可以看到。“祥林嫂可是异乎寻常,他们说她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轿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擒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阿呀,阿弥陀佛,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布还止不住血呢。直到七手八脚的将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还是骂,阿呀呀,这真是……”
她的反抗激烈,一路嚎,一路骂,而且“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布还止不住血呢。直到七手八脚的将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还是骂”,即使是来自卫婆子的转述,读者依然感受到这个女人的挣扎,这种挣扎固然可以说她受到了贞洁观念的束缚,但也应该理解为这是一个女人的不服从、不认同——面对强迫,祥林嫂发出了嚎叫,甚至以死相逼,但是,她有别的办法吗,只能再一次向命运低头。
当然,《祝福》也写到了祥林嫂命运的峰回路转,“后来?一起来了。她到年底就生了一个孩子,男的,新年就两岁了。我在娘家这几天,就有人到贺家澳去,回来说看见他们娘儿俩,母亲也胖,儿子也胖;上头又没有婆婆;男人所有的是力气,会做活;房子是自家的。——唉唉,她真是交了好运了。”可是,不多久厄运再一次降临。丈夫死了,孩子也死了,被大伯赶出家。像一个轮回一样,一无所有的祥林嫂又一次来到鲁四老爷家。这应该是她第四次自救了,她渴望用劳动换取报酬,然后活下去,获得正大光明地劳动、参与祭祀的权利。然而,正如后来读者所知道的,这个权利又被无情地剥夺了。
祥林嫂最重要的自救手段当然是捐门槛。那是第五次自救,她希望获得赎罪的机会,希望获得某种劳动权。又一次失败了,于是便是第六次,她与叙述人劈面相逢的发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此时,这个女人多么渴望获得终极意义上的精神救赎,但是,最终她没有获得她想要的答案。没有人能给她答案。事实上,捐门槛后她依然没有得到祭祀权。一次次压迫,一次次反抗,某种意义上,《祝福》讲述的是一个女人不断反抗、不断挣扎、不断被掠夺直至一无所有的故事。
责任编辑:梁佳
校对:刘威
声明:久久散文网为非赢利网站,文字及图片版权均归作者所有,如相关信息侵权与违规请与本站联系,将在三个工作日内处理。
本文链接:https://www.99sanwen.com/n/13523.html